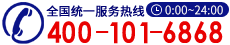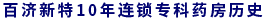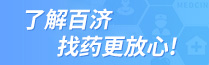您現在的位置: 百濟新特藥房網首頁 >> 戒煙 >> 戒煙日記
老伴戒煙
- 來源: 李秀珍 作者:百濟動態 瀏覽: 發布時間:2010/3/25 11:03:00
上世紀50年代初,我還是小青年時,從一本書中看到了吸煙的害處。當時我想,如果我找對象一定不找吸煙的。23歲時我和現在的老伴相識了,其他條件我都滿意,但他吸煙,于是我把那個想法如實地告訴了他。他聽完后,沒有在我面前說任何豪言壯語,更沒有做任何許諾與保證,但以后,我每次和他再見面,從沒有見他抽過一次煙,就是結婚以后他也不再吸煙。
不幸的是,1959年當我懷第二個孩子時,他被扣上“嚴重右傾”和“反彈”的帽子,受到撤職并開除黨籍的處分,送到一家工廠勞動改造。他對自己的處分是有意見的,就連續向組織寫自己的申訴意見。這期間我發現他晚上寫申訴材料時,又叼起了煙卷。我看他心情不好,也就不再管他吸煙的事。從此他越抽越兇,每天要抽兩盒最大的雪茄煙。他越抽臉色越黃,并經常咳嗽有痰,小小的居室內經常煙霧繚繞。十年動亂中他受到更大的沖擊,吸煙更多。我當時知道吸煙如同慢性自殺,但我不忍心加以阻止,因為我理解他受到冤屈后那種壓抑的心情,我知道吸煙是他用來減輕心中苦痛的手段。我甚至在他被關押被批斗時,還想辦法托人給他帶去香煙。
1978年黨中央撥亂反正,極“左”路線受到批評。我向他提出“如果給你真的平反,落實了政策,你是不是可以不抽了”的要求,他當時沒有回答,我也沒繼續往下問。后來他終于拿到了平反書,但我看他還吸煙。
然而沒過多久,有一天,兒子突然對我說:“媽媽,我爸爸已經好幾天沒有吸煙了。”我說:“是嗎?我還真沒注意。”后來我一問老伴,才知道他已經戒煙半個月了。從那時起到現在,他從未再抽過煙,長年的咳嗽也不治而愈。我高興極了,我佩服老伴的堅強毅力。我向他說起這件事,他只是淡淡地說:“我記著咱倆剛認識時你跟我說討厭吸煙的話,我不能讓你寒心。”